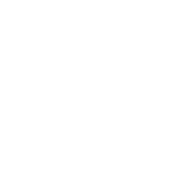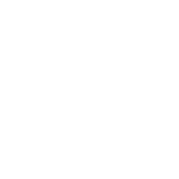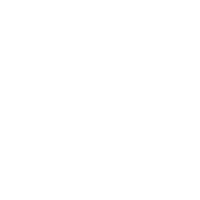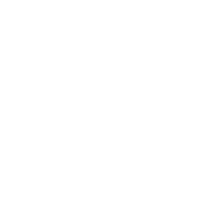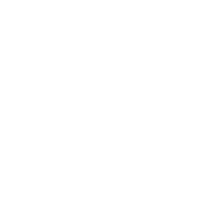从长沙到北平
一、在长沙
1929年夏天,三哥力成回家过暑假,正好我小学毕业。大概是大哥的意见,三哥过完暑假回上海时,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到长沙去上中学。当时长沙最好的中学是月云、铭德、湘雅,女子中学是周南。好的学校没有考上,进了一个中等的学校,叫兑泽中学。可就是这样一个中等水平的中学,我刚进去时读得也很吃力。记得英文课上,老师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在课堂上哭了一回。
兑泽中学的校长萧蓬慰(红卫),教务主任彭锦(景)云,还有一个党义教员,都是改组派。每个星期一周会上,都要在孙中山遗像前,背诵总理遗嘱、三民主义,约一个多小时。教务主任和党义教员讲党义,都要宣传改组派,宣传汪精卫,把汪说成是了不起的英雄。
这年寒假,我没有回家,补习了一个寒假,总算把功课赶上了。
进这个学校时,三哥把我的名字改了一下,音没有变,声阶的阶改成了口字旁的喈,成为邓声喈。这喈字是鸟鸣的意思,同声字联在一起有意义。同时,父亲为我起了个号,叫“鹤鸣”,说是从诗句“鹤鸣声喈”而来。1929年底,大哥又按“力”字序列,给我重起了个名字叫“邓力群”,与三哥邓力成排名,取群策群力之意。
从此,在父母兄弟亲属之间,口头上书面上都用邓力群这个名字。后来,入团、转党,也用这个名字。在北平,邓力群这个名字只有少数人知道。
关于力群这个名字,在延安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在马列学院,协助教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教员杨松编了一本《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公开出版时署名杨松、邓力群。鲁艺有位木刻家力群,写信给我说,他叫力群,我不应该用力群这个名字。我给这位姓郝的力群复信说,我在入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党内就知道我这个名字,这次公开出版这本书,杨松把这个名字署上去了。
1929年春,发生了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毛主席有一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中说的“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次战争。毛主席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指出,蒋桂两派新军阀在酝酿战争中。1929年4月,蒋、桂两派果然爆发了战争。桂系的军队从广西出发,攻岳阳未克,退回去。
蒋桂战争给红军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条件。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俘获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及其率领的官兵9000余人。红军杀了张辉瓒。他的头被钉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往下漂流,被国民党军队截住,连同尸体运回长沙开追悼会,逼令全体学生参加。
我在长沙兑泽中学前后一年半,实际只读了一年。
在长沙,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读新文学。印象深的有三本:蒋光赤的小说《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和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受感染。也读了郭沫若的新诗集《星空》、《橄榄》,印象深的是那些爱情诗,诗人同爱人一起数天上的星星。还读了翻译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没有读懂。读了这些新文学作品,写作文时也跟着学。记得那时还看过无声电影《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觉得很新奇。
1930年夏,蒋、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等处混战。阎、冯反对蒋,拥护汪,在北平召开了汪派国民党的扩大会议,声势很大。邓飞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时蒋介石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入关进北平,北平成为张学良的势力范围。阎退回山西。冯宣布下野,隐居泰山。其部下韩复榘主政山东。汪派转入“地下”。这时工农红军乘势“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毛主席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抒发了胜利豪情。
这年暑假,我同邓家琪、邓由善结伴回家,假期完了又结伴回长沙。走到衡阳,碰到从长沙出来的桂东同乡。他们说红军占领了长沙,国民党调了大批军队围攻。红军也动员很多农民进城,准备反攻。很快就要打大仗,长沙进不去,劝我们不要去了。我们就一起返回家乡。1930年下半年,待在家里,没能上学。
在这半年内,我还做过7天“堂倌”。事情是这样的:秋收后,流源乡要演几天戏。邓扬文说搭个棚子卖面食,可以赚钱。于是特意从县城里请来一个名厨,做包子、烧卖、面条卖。邓家琪、邓扬文和我,便做“堂倌”。做了7天买卖,结果除支付厨师工资外,一个钱也没有赚到。
1931年春,我又同邓家琪等结伴去长沙,继续在兑泽读初二上年级。
有一次去长沙最有名的一条大街八角亭买东西,见电线杆上挂一个木盒,里面放了一个人头,墙上贴了布告,围着一大堆人。听人议论说,这是一个红军的负责人,被杀害后拿来示众。当时感到国民党太残暴。大致同时,国民党在长沙为张辉瓒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强令各机关、学校结队去灵堂致哀。我随着兑泽中学的同学去了,但哀却没有。长沙八角亭,有几次人头示众,我看过两次。
如果说,国民党改组派是推动我走向反蒋道路的一个教员,那末,湖南农民运动是引导我走向反蒋道路的最重要的正面教员。我亲眼目睹,而且作为儿童团成员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些活动,深有体会。我们那里农会的领导人、小学教师邓兆雄,被反动军队抓走,押赴刑场,一路上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割了他的舌头,残忍地折磨他。他坚贞不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情况和影响、意义,是很有说服力的。
二、到北平
蒋奉战争后,邓飞黄和改组派的一些人,退到天津租界活动。冯玉祥每月给他200大洋维持生活。在租界中维持改组派的活动另有经费。
1931年暑假,大哥把母亲接出来,并要我转学北平。母亲带着邓力成(三哥)的大女儿帼英(7岁)到了长沙。邓建黄(四哥)从北平来长沙。这时邓力成已到吉鸿昌那里当参谋,也来到了长沙。我们一共5个人坐船到南京。从浦口坐火车,7月底或8月初到了北平。那时王荟君(大嫂)带着两个孩子(大的鼎元,3岁,小的平元,不到一岁),住在东城赵家楼胡同。我们到了以后就一起住在那里。邓飞黄和改组派一些人平常住在天津日租界,进行反蒋活动,星期六下午回北平家里。他家里有一个保姆带孩子,一个“老妈子”做饭。
三、汇文中学四年
三哥邓力成不久回吉鸿昌那里去了。临走前听他和大哥说,他准备给吉鸿昌递交反蒋意见书。四哥邓建黄在北平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准备继续读中学。
由于长沙的教学水平比北平低,我虽读了初中3个学期,但报考师大附中初二,未考上。报考汇文中学,考上了,但英文不及格。汇文当时规定,两门功课不及格还可以录取,及格的功课跟本年级上,不及格的功课跟下年级上。所以,英语课跟着初一年级上。我于9月初进了汇文中学,住在大哥家,做走读生。长兄如父。他长我20岁,管我比较严格,除学校的功课外,要求每周背一篇古文,每天还要写日记。他定期检查。
上学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掌管北平的张学良,在天安门旁三大殿里开了一次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会议。允许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我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参加游行,参加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汪精卫开始调子很高,但很快蒋汪合流。汪成为国民党的第二领袖,他手下的骨干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部、局级干部。
1931年11月或12月,大哥邓飞黄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接着又当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春天,大哥、大嫂、母亲和三哥的女儿帼英搬往南京。四哥也随同去南京上学了。
汇文是比较好的中学。大哥让我留在北平,住进汇文宿舍,继续在汇文上学。开始我有点跟不上班。1932年暑假我没回南京,又补习了一段功课。从初三上开始全部功课都跟上本年级了。
汇文中学一学年学费250元(银元),房租每月3元,二等伙食费每月6元,此外,衣服、书籍、零用每年60元左右,全年共需400来元。如果寒暑假回家,就要少一些。我当时的生活水平,在学生里是中等的。因为不会计划使用,每学期最后一两个月都会没有钱用。
我有时在汇文中学门口馄饨摊,吃两碗馄饨,一个烧饼,一根香肠,花21个铜板。味道美极了。我老了在医院吃过几次“馄饨侯”,味道比那时小摊子上吃的差得多。在零花钱方面,主要是看京戏。我最爱看马连良,在前门外大街的一个戏院。每次花二角五分钱,看戏回来,去吃炒面、炒饼。后来,有个戏剧学校,七八岁开始学,学了6年以后就登台,在吉祥戏院演出。我和同学都去看,坐在后排,票价便宜,要不了二角五。
大哥家搬到南京去时,托他3个朋友照顾我。一个是贺楚强,是冯玉祥手下人。冯给邓飞黄的钱,多半是经他送来。他那时住在公寓里,我去看过他三四次。一个是向达,那时在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住中南海。我去他家两次。还有一个是彭海安,是一个大学的讲师,妻子是美术教员。我去过他家一次。他们在1933年初或再早些的时间,都先后离开北平去南方了。
16岁这年,处在一个转折关头。留在北平而未去南京,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如果去了南京,我走的道路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也会参加抗日,参加革命,但走的路径会不同。
汇文中学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教会学校,功课很紧。星期一至五,每天上7至9节课,星期六上午4节课,下午没有课。星期一至五每天晚上,要自习两小时。汇文各种设备比较完善,有宿舍,有食堂,有很好的运动场,高级的篮球场,有体育馆,有讲台(主席台),还有一层一层的看台。除比赛外可以开会。如果不买东西,一两个月不出校门也可以。
我很爱好学习。从初三上开始,成绩好起来了。汇文学生比较多,每学期按成绩编一次班,最好的编为甲班,依次编为乙、丙、丁各班。我从初三到高三都编入甲班。
在汇文中学住校后,生活很有规律。起床后晨练、早读,每天读英文。晚自习主要做数学题。每次一个多小时就可做完。习题再难我都是自己做,从不求人帮忙。月考、季考、期考,我都不用临时抱佛脚、开夜车。平时还利用时间看不少课外书籍。
我在汇文中学4年,读书是用功的,在初中和高中,都遇到了好的数学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好,抓得紧。课后都留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批改。
1933年以前,学好功课是第一位的,课外主要看小说。这时我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当时出版的书,翻译过来的旧俄、苏联、英国、法国的书,我读得很多,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科罗连柯的《盲音乐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不少小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比塞的《斯大林传 ———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等等。中国的左翼作家,鲁迅的《呐喊》、《彷徨》看了,鲁迅的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花边文学》,每年都出版一本到两本,我都读了。还有他的翻译作品,如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也读了。茅盾反映大革命时期斗争情况的小说《虹》、《蚀》以及《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郭沫若创作的、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研究著述,如《青铜时代》等,也都读了。还有郁达夫、张天翼、林语堂等的书。1935年、1936年还读了曹禺的《雷雨》、《日出》,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当时的进步书籍,出一本,买一本,读一本。1934年开始看社会科学的书籍,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书,虽然不太懂,还是认真地做了阅读笔记,并且推动关系好的同学读这类进步书籍。
四、1933年春:思想转折点
这时读书,和在桂东老家不同,桂东是读旧小说,从长沙到北平,是读新小说,读进步刊物。在汇文中学的同学中,以至于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同事中,比我读书多的,还比较少见。
当时读的这些书,对我思想有很大帮助。读书增进了反日情绪,反日情绪又加强了读书兴趣。这是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准备。但促使我思想激进的根本因素,是时代的风云,现实的刺激,加上我同一位革命青年的直接接触。我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抗战只有靠共产党,不能靠蒋介石、汪精卫。
1933年春天,可以说是我思想的转折点。
当时整个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际。中国是半殖民地,与印度等受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殖民地不同,中国受多个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被他们控制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搞得国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东交民巷有各国的军队,我们上学经过的几条街,都是外国军队。现在的东单公园当时是外国兵营的操场。汇文中学在崇文门,出来就见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去妓院嫖妓的,各国的人都有,搞得乌烟瘴气。经常见到外国人打我们的车夫。大同医院旁边是日本兵的驻地。电车道旁也是外国军队的一条跑道。天天亲眼目睹这些情景,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会受到刺激,感到愤慨。我在汇文中学的时候,爱国热情高涨,参加了一些反对日本侵略的救亡活动。但思想目标还不很明确。
有一位远房表哥,名叫胡平,在京是中学读高中。那个时候他大概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可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他很热心地从思想上帮助我,推动我进步。他带我去看进步电影,引导我看进步书籍。在他的影响下,当时认识到要抵抗日本侵略,必须打倒国民党蒋介石。1932年以后,同他一起在东安市场买到了地下党出版的一些秘密刊物、小报,上面登载着各地红军发展的消息、党对抗日救国的主张。由此我把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产生了加入革命组织的愿望。1933年春,我正式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他说可以,过些日子找个人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没想到过几天,他就被捕了。
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胖子,看上去像个密探。我有点纳闷,也有点着急,心想这样的人来找我干嘛?他偷偷地把一封信塞给了我。原来是胡平捎来的,说他被捕了,让我给他捎点吃的东西,同时给捎信的人一两元大洋。这下我才知道,他和我谈话没几天,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时被捕。判决后,关在草岚子反省院,与薄一波他们关在一起,就是所谓61个人集团的一员,他那时还没有入党呢。在这封信上还提到:他有两个书架和一张靠背椅,寄放在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让我去取。我后来去了。这个人叫孙光。取东西时,我向他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他说,你还年轻,不要着急。没想到,过了几天,孙光也被捕了。
后来,我买了东西,到草岚子监狱探监。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那个地方有很高的围墙,走近那里就听到镣铐声。见到了胡平,他戴着手铐、脚镣。看了这样的情景,我心都碎了,当时我就大哭了一场。以后每隔一两个月,我就去给他送点东西。他特别喜欢吃咖喱角。以后我对咖喱角有感情,就是这个原因。每次我都买一两斤送去。我以为这些点心,他可以吃三五天或一个星期。但是他来信说,他把这些点心都分给难友,每人一份,实际上他自己没吃到几块。这个经历,增强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和仇视,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敬仰。
五、1933年暑假在南京的见闻
1933年暑假,我回南京,见到了父亲。知道这年上半年,红军到寨前,要去捉一个大地主,地主跑了,恰好我父亲在他家做客,被捉了去。有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听说是邓飞黄的父亲,对他比较优待。后来知道这个负责人是袁任远同志,原在河南做地下工作。国民党反革命后,冯玉祥对共产党员实行礼送出境的政策。邓飞黄执行这个政策,送走袁任远和其他几个同志,没有为难他们。父亲在红军那里待了十几天,出了300大洋,就放回来了。过后,父亲就到了南京。
这次见到父亲,出乎意外,他对红军,一句坏话没说,倒说了一些好话。说红军官兵关系好,军民关系好,纪律好。那时报上正刊登一些贪污案件。他说红军那里没有这些事情,认为红军、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这时三哥也到了南京,并把三嫂接了出来。他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干事。四哥建黄,考上了南京的金陵大学。
在南京接触了一些在国民党里干事的公务人员。他们的生活一是打麻将,二是玩歌女,三是互相请客吃饭。我有时去看他们打牌,也去过一次歌厅。主要的暑假生活是同大哥、四哥每天下午到中山陵游泳。大哥不打牌,不玩歌女,不抽烟。但是连他在内,我没听他们中有一个谈过国家存亡、民族危机。我深感到,不能指望这些人来挽救民族危亡。
六、父亲去世
1934年上半年,学校宿舍住不进。恰好有个名叫欧阳镇的同学,带了老婆、丫头在苏州胡同租了房子住,愿意把多余的几间转租。我约了几个同学住到那里去,雇了一个老头子做饭。一直住到下半年寒假。
这年暑假,我又回南京。生活情况与前一年基本相同。发生变化的是父亲得了鼻癌,在南京、上海都治不好。8月下旬,同我一起来北平医治。在协和医院、德国医院愈治愈坏。到12月,三哥把他接回南京。不久病危,要我回去探望。我们兄弟几个在鼓楼医院看着父亲咽气。抬回家里,我摸他腹部还有点温热,跟妈说,父亲没有死。当时父亲58岁,我19岁。
在南京,父亲有一张半身照片,全家三代合过一次影,可惜姐姐不在。照片上父亲留胡子,一派自信、满意的神态。“文化大革命”中,照片被红卫兵抄去、示众。这也不奇怪,在他们眼中,肯定认为他是个封建余孽。
七、我打定了跟共产党抗日的主意
1934年寒假,我到南京去。我的日记本也随身带去了。大哥从我的日记中,从与我交谈中,看出了我的思想变化。他同我作了一次在他说来是诚恳的谈话。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他不反对,只是希望我在大学毕业、独立生活之前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他说他自己原来打算做学问,只是因为家庭负担,因为答应过父亲负责任给我们兄弟上学,才不得不投身政界,一直到现在仍不能做学问,是一生最大的遗憾。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热望我在学问上有成就,以弥补他的遗憾。他希望我学水利。他说黄河为害中国几千年,多少朝代、多少人都没治好,如果我能下决心学水利工程,将来能主持治好黄河,就会造福于几千万人。他说只要我有这个决心,在大学毕业后,他可以送我去留洋。只要真正有了学问,有了本事,国民党要用,共产党也要用。
为了让我走他为我安排的道路,断绝我对共产党的信念,他告诉我,经过蒋介石军队的“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使将来共产党能发展、能胜利,至少也要几十年以后了。他指着桌子上的一本书说,蒋介石军队“打败”红军的事情,书上写得很详细,让我好好看看。
作为兄弟,他这种心情我是尊重和理解的,但从我当时的思想倾向来讲,已听不进他的这些教诲了。他要我看的那本书,我连动都没有去动一下,让它留在桌子上。我转身就走了。
后来,大哥对家里人说,力群这个人,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不管你说多少话,讲多少道理,也改变不了他。
1935年暑假后,学校宿舍空了。我和住在苏州胡同的几个同学又一起住进了学校。
当时,日本对华侵略日益猖狂,冀东反共政府成立,华北五省酝酿“自治”,天上日本飞机进行侦察,地上日本陆军武装演习。处处时时都显示出亡国的危险已降临到全中国人民的头上。这时我对邓飞黄为我指出的前途,虽然没有完全断念,但是整个形势的发展,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也愈来愈无法安稳地读书了。这时,我已经确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跟着共产党抗日,为解救民族危亡奉献自己的青春!
我的大哥则跟我走着不同的路。大约是在1935年末或1936年初,蒋介石排挤汪精卫,汪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他下面的大将谷正刚、谷正鼎投靠CC。大哥邓飞黄也随之倒台,辞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准备留洋学习。
(未完待续)
(特邀编辑:陶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