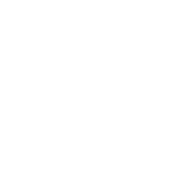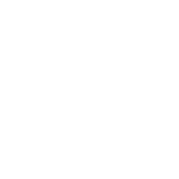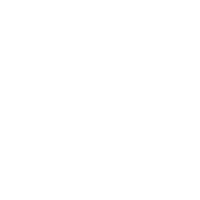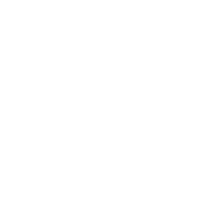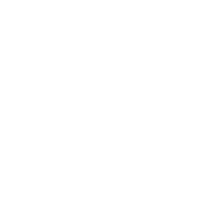熊爱军
邹韬奋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忠贞的民主主义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家,一生爱国,以笔代枪,不畏强权,经历坎坷,六次流亡,颠沛流离,不屈不挠。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是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典范。
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从1922年开始,邹韬奋在中华教育社专门从事职业教育工作。1926年10月,担任中华职业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主笔的王志莘另谋他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的推荐下,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踊跃地走上记者编辑的岗位,实现了他一直以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愿望。《生活》周刊旨在传播职业界的消息和言论,刊载有关职业教育和职业修养方面的文章。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从内容到排版等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发行数量也随着内容的改进而逐年增加。邹韬奋接办3年,订数2000多增到4万份。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东三省。邹韬奋于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本着爱国热忱,反复向当局呼吁,向大众揭露亡国危机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倾尽全力,把《生活》周刊作为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并督促有关各个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一致抗日。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蒋光鼐和蔡廷锴奋起反击,开始了著名的淞沪抗战。上海的抗日救国浪潮日益高涨,邹韬奋和他领导的《生活》周刊的同事们,都成了抗日救亡的积极参加者。这时的邹韬奋既要奔赴前线慰问将士们,又要参加后方的各种服务活动,白天奔波不止,夜晚又写作不停。他恨不能分身为几人投入这抗日热流,以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生活》周刊也变成全国闻名的坚决主张抗日救亡的刊物,销量激增到12万份,这是当时任何报刊都没有达到的。同时,邹韬奋深深感到自己主编的周刊,已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又加编了《紧急临时周刊》。
国民党当局当时正在对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进行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围剿”,对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报刊视为眼中钉。黄炎培是《申报》的董事长,而《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都与黄炎培有关。蒋介石把黄炎培申斥一顿,要《申报》和《生活》周刊改变态度,拥护国民党,否则就要查封。在蒋的高压下,《申报》再不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关于《生活》周刊,黄炎培要求邹韬奋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声明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关系。邹韬奋坚决拒绝改变政治态度,同意与职教社脱离关系,由他自己负责办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生活》周刊的态度,也是前后变化的,先是称赞,后是恫吓,进而下令禁止邮寄,直到最后查禁。邹韬奋在这些伎俩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1931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奉命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进行了4个小时的辩论。胡宗南企图对邹韬奋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邹韬奋义正言辞,毫不动摇。关于抗日问题,邹韬奋说,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暴力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关于《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邹韬奋指出,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对中国前途,认为只有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胡宗南要求邹韬奋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则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1932年7月2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发表《我们最近的趋向》重申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随即遭到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诽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邮递,后又在全国禁止邮寄,有的学生因购阅这个刊物而遭逮捕。蔡元培曾经致电蒋介石进行解释,均遭拒绝。后又有人为此事进行“疏通”,蒋介石拿出合订本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批评国民党的地方,都有红笔划了出来,并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尽管如此,在热心读者多方面的帮助下,《生活》周刊的邮包绕过军警特务的监视,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渠道,大捆大包地运往各地。
正当《生活》周刊遭受到种种压力的时候,在胡愈之的建议下,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有了生活书店就可以出版书籍和其他刊物,可以扩大宣传阵地,而《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封闭的可能。有了书店,刊物即使被封,阵地仍然存在,可以换一个名称继续出版刊物。
1932年12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鲁迅和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3年 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经常受到盯梢、恐吓。他每天上下班几次往返经过法国公园,尤其到了晚上,天黑路偏。朋友们替他的安全担心,都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他一想也是,不保存自己,怎能有力打击敌人。可往哪里躲呢?何处才是安身之所?看来出国才是唯一的去处。1933年7月,邹韬奋离开祖国,开始了第一次流亡。
二、“不做陈布雷第二”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从美国回到上海。邹韬奋回国之际,正是国难更加危机之时。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后,1935年5月开始,日军大批直接入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对于友邦,务敦睦谊”。
邹韬奋出国后,生活书店在徐伯昕的经营下蒸蒸日上。《生活》周刊早已于1933年12月被迫停刊。于是,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大众生活》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优良传统,把办刊物和民族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作宣传的重要目标,这是邹韬奋高高举起的旗帜。他决不会为反动势力的威胁而摇摆或改变。但是《大众生活》共办16期,历时3个多月就被国民党封闭了。
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邹韬奋立即予以最热烈的声援。《大众生活》以最大篇幅来反映这个运动,国民党政府十分害怕,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大众生活》,并对邹韬奋进行毁谤和恫吓。
在短短期间连续发生几桩预谋事件,目标均集中在邹韬奋身上。
第一桩,特务一再造谣,诬说邹韬奋侵吞1932年《生活》周刊代收各界援助马占山卫国捐款,邹韬奋特请律师代他在报刊上再一次发表启事,并把当年会计师所出证明书一起公布,以事实粉碎这一诬陷。他说:“他们徒然心劳力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污蔑是不足畏的。”
第二桩是,蒋介石指派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为说客,找邹韬奋说话,中间人是邵洵美,约见地点在邵洵美家里。邹韬奋同刘、张一见面,张道藩就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邹韬奋静心倾听,却始终不得要领。刘健群则鼓吹的是“领袖至上”一套,不管中国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一切全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刘健群进一步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邹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同时更明确地告诉他们:“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喊准备,实属南辕北辙。”要说抗日救亡问题,他说:“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对于所谓“领袖脑壳论”,邹韬奋则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领袖观便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领袖观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这场辩论结束,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刘健群、张道藩回南京不久,杜月笙又奉蒋介石之命,准备“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当面一谈”。邹韬奋不为权势所动,坚决回绝。一个和蒋介石走得近的银行家对邹韬奋说:“你拂逆了老蒋的意志,看来只得再度流亡了。”邹韬奋的“胆大妄为”确实令蒋介石大为恼火,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处境危殆,邹韬奋考虑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前次流亡,负债尚未还清,在经济上无力远行,他只好出走到距离较近的香港。时隔几年后,张群在重庆向邹韬奋无意间透露:“那次接你到南京,是蒋寻奇才,因为陈布雷太忙,要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蒋介石竟要邹韬奋做“陈布雷第二”,殊不知邹韬奋是硬骨头。
三、“转移工作地点,向前努力奋斗”
办一种合于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纸,是邹韬奋长久的愿望。1932年,《生活日报》在上海没有办成,1936年6月7日,终于在香港的贫民窟诞生了。《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55天,共出5期,日销量为2万份。这比当地的日报五六千份好多了。但是由于香港偏离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没法满足读者的要求。8月1日,《生活日报》迁移到上海,邹韬奋不顾个人安危,也跟着回到上海,进行报纸的恢复工作。但因国民党政府不给办登记手续,《生活日报》没有再和读者见面。
团结、御侮是救国会忙碌的两件大事。邹韬奋积极参与援助绥远抗战,积极支持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在《生活星期刊》发表社论积极声援。当时,有朋友告诫邹韬奋将有被捕的危险,邹韬奋说:“我以胸怀坦白,不以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这时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1936年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却突然地被捕了。
1937年8月3日,邹韬奋从苏州狱中释放,回到上海,立马投入到全国团结御侮的活动中。8月9日《抗战》第1号问世,还增加出版6天1期的《抗战画报》。同时,邹韬奋还兼任《国民周刊》的评论委员会委员,统由生活书店发行。他以生活书店和《抗战》三日刊为据点,利用宣讲的嘴和锋利的笔,对时局作出敏锐的观察,对各方动向作出深刻的分析,批判汉奸和准汉奸的“亡国论”,批判急于求成的速胜论,驳斥汪精卫亲日派的投降谬论。
淞沪抗战,上海战局支撑3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邹韬奋和他的挚友以及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备西撤,重点是重庆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内地开设分店。11月27日,邹韬奋坐一条法国船离开上海。邹韬奋对这次流亡的心情曾说:“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二两次以及以后几次都迥然不同。”这次是因为“转移阵地的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惟其如此,“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
四、“我无法保障它,还能保障什么!”
邹韬奋经常向人说:“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一到武汉,他全力以赴抓紧《全民抗战》的编辑发行工作,以新的内容,在新的天地里,同更多的读者交心。正如金仲华所说,邹韬奋“爱刊如命,办刊成癖”。他的“爱”和“癖”都是着眼于读者。不管他多么忙,他都挤出时间,阅读读者来信和接待读者来访,他从不让读者失望。因为,他一直把读者看作是激发自己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办店和办刊一样,不仅是他进行抗战的斗争据点,也是他从事文化事业的基地。在上海时,刊店是合一的,从武汉到重庆后,在抗战的大形势下,邹韬奋不失时机地发展生活书店,经过努力,不到两年时间里,在50多处开设了分店。这是生活书店发展的鼎盛时期,邹韬奋忆起这一时期时,一方面感到兴奋和欣慰,另一方面也回味着其中的辛酸和苦辣。他在《抗战以来》中写道:“往内地建立工作据点的同事,号称‘经理’,实际上等于流亡。因为交通拥挤,曾有同事乘船被挤得落下水去,勉强获救,得全生命。有的同事因经济困窘,登岸后即在码头露宿一宵,然后努力建立新的工作据点,执行‘经理’职务。”
生活书店不断扩张及大量进步书籍的出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于是生活书店和邹韬奋便成了他们连连打击的目标,工作人员被捕,大批分店遭封。国民党对生活书店如此摧残,邹韬奋愤怒不止,在短短几个月内,成批封闭书店和逮捕人员,这不可能是各地随意胡来,一定是国民党中央有密令下达。为此邹韬奋到中宣部,找到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请他们主持公道。邹韬奋说明“生活”并没有不服从法令,也没有不接受纠正的事实。叶、潘佯说他们不知道此事,是“地方党部的行为”,让邹韬奋静候“查明具报”。其实,这是推托的谎言,有朋友谈起从国民党中央党部传出的消息:说中央党部已决定先封闭“生活”的各分店,然后进而封闭重庆总店,并且他们还看到了这种密令。
国民党中央党部对生活书店看作既定拔除的眼中钉,叶楚伧和潘公展公然提出:要生活书店和正中书店及独立出版社联合,在3个机构之上组织一个总管理处或成立一个董事会,主持一切。这样,一则可能使党部放心,二则可由竞争而增加效益,三则可避免各地方当局对“生活”为难,得到依法保障。
为了捍卫生活书店,邹韬奋曾访陈布雷。当听了邹韬奋的诚恳讲述的事实之后,陈布雷说:“韬奋兄,党里有些同志认为你们所办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妨碍了他们所办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邹韬奋对这种说法指出:“事业发展有其本身积极努力的因素,应该在工作努力上比赛,不应凭借政治力量给予对方以压迫和摧残。”
徐恩曾是邹韬奋从中学到大学的机电科的同班同学。按徐的身份和地位,对共产党当然破口大骂,这并不奇怪。而邹韬奋向徐恩曾说明,国民党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如此不合理,并直接问他:“依我们老同学的友谊,彼此都可以说老实话,你是主持特务的,依你所得材料,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微笑着说:“我‘跟’了你七年之久,未能证明你是共产党。”邹韬奋说:“既然如此,你何必对我说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话?”徐恩曾很直率地说:“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邹韬奋说:“我的工作是完全公开的,无论是出书或出刊物,无论是写书或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都经过政府设立的审查机关的审查,审查通过的文章不能再归罪于我吧?如果我们做的工作是为共产党工作,审查机关是国民党的机关,为什么通过呢?”徐恩曾说:“有许多事情不能见于法令,与审查的通过不相干,要你自己明白其意而为之。”邹韬奋老实地对他说:“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能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遵守国家法令就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私人或私党的走狗!”徐恩曾希望邹韬奋加入国民党。邹韬奋说:无缘无故连封10多家书店,把无辜的工作人员拘捕。“在这样无理压迫下要我入党,无异叫我屈膝,中国读书人是最讲气节的,这也是民族气节的一个根源,即使我屈膝,你们得到这样一个无人格的党员有何益处?”关于“生活”,徐恩曾说中宣部主张和党办的正中书局等合并,是表示国民党看得起“生活”,应该赶紧接受!邹韬奋当然无法“仰承旨意”,也就谦然结束了这番谈话。
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50多个分店,在国民党打击摧残下,只剩下6个分店。
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中央党部把重庆各报馆请来制定宣传要点,讲明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一些反动报刊迎合国民党要求,大骂新四军,只有邹韬奋卓尔不群,自成观点写成一篇。正准备发表,不料国民党新闻检查时,全文被审查官扣留,而且,勒令《全民抗战》停刊。紧接着生活书店在昆明、成都、桂林、贵阳等5个分店全被查封,只保留重庆一个分店了。同样,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所有分店,除重庆外,也被封闭了。邹韬奋心急如焚,食眠俱废。2月21日晚,他匆匆到了沈钧儒家,神色有点仓皇,手里拿到几份电报,眼眶里含着带怒的泪水,向沈钧儒说:“这是什么景象!一点不要理由,就这样干完了我的书店!我无法保障它,还能保障什么!我决意走了。”他决意辞去国民参政员。他在辞职信中写到:“二三年来之实际经验,深觉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精神上时感深刻之痛苦,但以顾全大局,希望有徐图挽救之机会,故未忍遽尔言去耳。”生活书店努力抗战建国文化“十六年之惨淡经营,五十余处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毁。”“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侮。即在会外欲勉守文化岗位,有所努力,亦为事实所不许。故决计远离,暂以尽心于译著,自藏愚拙。临行匆促,未能尽所欲言。”2月25日,邹韬奋在夫人沈粹缜的依依不舍中告别重庆。刚刚到达桂林,当地国民党特务就接到电报:扣留邹韬奋。不等特务们作出反应,邹韬奋就乘飞机去了香港。
五、“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
邹韬奋出走香港并不是消极的避难,而是利用自己的口和笔,进行业已熟练的战斗。他一到香港就与先抵达香港的范长江,作了一次心情舒畅的交谈。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见解,彼此都是献身于新闻记者所从事的事业。范长江以中国新闻社创办人的身份,到了香港与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和港绅邓文田等筹办了《华商报》。在范长江的鼓动下,邹韬奋为《华商报》撰写长篇,把他在重庆参加政治活动所接触的事实做一番检讨,以助民主运动。这就是长篇连载《抗战以来》。同时,他还为《华商报》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后来编辑为《对反对民主的抗争》一书。
1941年4月间,大批文化人从重庆桂林等地纷纷到了香港,报刊也顿时增多起来。除了《华商报》外,参政员梁漱溟也来香港筹办《光明报》,黄炎培创办《国讯》旬刊。一些救国会留港会员创办《救国丛刊》。香港的文化空气盛极一时。正是这个时候,邹韬奋把在上海出刊被查禁的《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复刊。邹韬奋除了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外,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编刊物和写文章中。当时,他在写信给沈钧儒说:“每一天要写若干字数的文字,还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放下笔杆,倒头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他写作之勤,文章之多,真是紧张得恨不得分身去承担。有人说他“性急”,他自己也承认“性急”的缺点,但与他一起相处、亲自目睹他这段紧张生活的茅盾则说:“我倒觉得韬奋的嫉恶如仇、说干就干、充满信心、极端负责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九龙、香港被日本占领。邹韬奋的特殊身份成为日本间谍和汪伪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务所关注的对象。在此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邹韬奋不断地搬迁、躲藏、流离失所,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在这种状况下,邹韬奋不仅不能编刊,写作停止,就是必要的食宿也成问题。
而在此时,一场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大救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同日,周恩来按中共中央指示,向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两次急电布置工作:估计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期,而上海交通已断绝,因此,在港人员的退路,除去广州湾和东江外,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将撤回内地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戏剧界的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可去马来亚。少部分能留港者尽量留下,但必须符合秘密条件。继而又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情况,并叮嘱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以便使他们安全离港。他特别关注当时国民党特务准备迫害的柳亚子和邹韬奋,又电南委书记方方,要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他们的安全。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中共在港的存款中开支。
12月9日,周恩来在发出上述急电的第二天,又向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致电,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同志具体布置。同时,分电南委、桂林统战委员会,要他们作好接应及转送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对撤出人员的去向、工作、家属的安排、交通生活费用的支付,留港人员的工作等等,作了详尽的指示。
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组织在港同志投入工作,及时同南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桂林统战委员会等取得了联系,并由廖承志、张文彬在香港、惠阳召集有关领导人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邹韬奋当时并不清楚上述具体详情,只知从九龙开始转移起,以及每次变换地点都有朋友尽力相助,而且都那么自觉,那么积极,那么热情,他们并没有由于战争的困难而感到委屈。
经中共地下组织周密安排,1942年1月11日,邹韬奋离港奔赴东江游击区。他们爬高山、涉湍河,巧妙通过日伪的盘查,混过关卡,最后来到一个叫白石垅村的地方,东江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邹韬奋会见了游击纵队司令员曾生和政治委员尹林平。他们热情接待了邹韬奋,转达党中央的慰问,并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在欢迎会上,邹韬奋自喻是跟随“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阵地回来。在发言中,他一再强调地说:“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今后我一定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
在东江,生活困难,战斗激烈,邹韬奋全然不顾,依然进行忘我的工作,作报告、写文章,帮忙编辑《东江民报》。可是,不久,新情况出现了,东江游击司令部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说国民党当局已秘密下令通缉邹韬奋,指令各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中共中央南方局嘱咐,务必设法保证邹韬奋安全,党组织征得邹韬奋同意,让他去广东梅县乡下暂住。
六、“到八路军、新四军方面去,参加革命斗争”
1942年4月,邹韬奋以香港某某商行股东李尚清的名字寓居在梅县江头村陈启昌家中。
在梅县乡下,邹韬奋过着紧张而又充实的隐居生活。邹韬奋非常想念桂林的夫人和孩子,还曾想把他们迁过来,与他一起共享隐居之乐,可得知他们住在桂林郊区,不宜立即移动,通信亦不能直接邮寄,迁动只待时机了。
8月间,邹韬奋的战友徐伯昕专程从桂林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邹韬奋的情况。周恩来认为,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下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建议邹韬奋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9月中旬,中共党组织派原生活书店的干部冯舒之来到梅县迎接并护送邹韬奋北上去上海。正在这时,中共华南工委也得知,国民党特务已侦察到邹韬奋隐居梅县乡下,增派刘百闵亲往,加紧侦缉,沿途关卡哨所,都放着邹韬奋的照片和密缉令。中共地下党组织布置的任务是,必须立即设法把邹韬奋护送出去。邹韬奋知道再住无益,弄不好连累好客的主人,接受党的劝告,到苏北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斗争,以贡献自己的一切。他非常感慨地说,他“过去主张实业救国,提倡职业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想;后来主张放弃武装,与蒋介石和平协商,联合救国,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他也十分愤慨地认识到:“我毕生办刊物,作记者、开书店,简直是‘题残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了,但政权军权还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千万人头落地!千万本书籍杂志焚毁!连我这样的文弱书生、空谈爱国者,他都一再使我流离失所,家散人亡呢!我现在彻底觉悟了,我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去,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
9月27日,邹韬奋告别了江头村,又走上了流亡的路途,前往沦陷区上海,然后从那里到苏北解放区,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流亡,也是最后一次。
1943年3月,邹韬奋秘密回到上海治疗耳病,1944年7月,因耳癌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