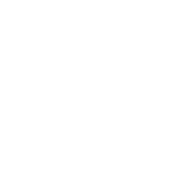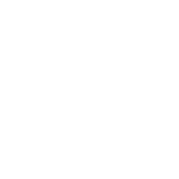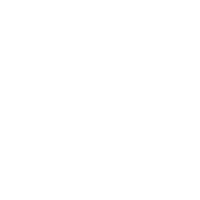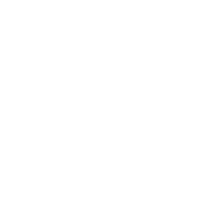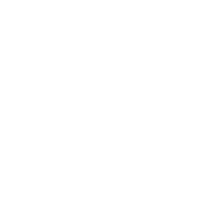倪 蛟
关露,原名胡寿楣,20世纪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电影《十字街头》中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就是由其作词的。关露不仅是乱世中的才女,也是谍海战线的“红色特工”。她接受特殊使命,因信仰而打入日伪情报组织,顶着“汉奸文人”的骂名献身党的隐秘战线,为民族解放而牺牲个人名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关露屡遭打击,含冤入狱,但对于党无限忠诚,用尽一生始终如一地践行在党旗下的铮铮誓言,正如她向党赤诚告白的那样,“我的生命,没有半点灰尘”。
蜚声上海滩的左翼女诗人:诗歌创作“是一种强有力的战斗武器”
关露的文学梦萌发于其年幼时的家庭环境,而后在大学时代的进步思想引领下茁壮成长,进而成为蜚声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和中国文坛的左翼女诗人。1907年,关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在其母的启迪与指引下,接受的是四书五经、古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且其本人热爱读书、才思敏捷,在文学上展现出独特的天赋秉性。幼时的学习经历让关露与文学结缘,但真正影响关露后来诗歌创作志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求学生涯。
1928年,关露化名胡寿华考入民国时期首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哲学系)。当时的中央大学可称得上是孕育新诗人的摇篮,闻一多、徐志摩等著名教授倡导新诗,一些中大学生也热衷于创作新诗。受到这些新诗人的影响,关露便迷上了新诗,热衷于新诗的表达方式和内在情感,“能够装载我底生活情调,能够表现我底情感的东西是像郭沫若、徐志摩所写的那样,自由而新颖的词句,不是那些限字限韵的旧东西”。同时,关露还大量学习外国诗歌,其第一首新诗的灵感就来源于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她模仿维特自杀前向夏绿蒂吟诵的诗,以颂扬的口吻哀悼想象中的一个男孩子。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大时期,关露在思想上逐步由热爱文学的小知识分子,转向具有进步思想的女青年。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和启发,关露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初,关露和进步女学生一起驱赶女生宿舍指导员———当时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教授英文的留美华人李玛丽。时任中大校长朱家骅因“驱赶”事件对关露耿耿于怀,于同年5月以关露没有正式的中学文凭为借口将关露开除。就此,关露离开了学习和生活三年的中大校园,转向上海,迈入文坛,开启了复杂多变、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
到上海后,关露经中大进步同学介绍,参加了上海民众抗日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的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关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成员,并在党的领导下其诗歌观日渐成熟,在《用什么方法去写诗》一文中,她鲜明主张诗歌当以大众为对象,以大众生活为素材,创作任务应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前进”,“是一种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对左翼作家的血腥镇压,残忍杀害了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翼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之下,作为诗坛年轻的左翼诗人,关露不惧生死安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热情投身大众化诗歌运动,“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当中”,鼓动工人阶级开展反奴役、反剥削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关露发表在《新诗歌》上的诗有《哥哥》、《马达响了》、《机声》等。如反映工人悲惨命运,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罪行的《马达响了》(1934年7月):
马达响了,
织绸子的机器开动了,
我们千百个人都随着机器开动了。
血,汗,
一点,一滴,
绸子,
一尺,一寸,
用机器去织绸子,
用血汗去滑动机器。
日班,
夜班,
从天明到日落,
从日落到夜半,
一点,一滴,
一尺,一寸。
瘦了,
我们瘦了,
血汗变成了绸子,
绸子变成了资本家的资本。
一点,一滴,
一尺,一寸,
机器开动了,
我们千百个人也开动了。
像《马达响了》这样的诗歌直接反映了工人的实际生活以及他们与资本家的斗争,且在艺术形式上贴近工人群众,受到了广泛好评。此时的关露,不仅用诗歌去战斗,而且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她关注女性解放和生活状态,脱下旗袍换上女工服装与纺织女工们谈心,主动与女工们交朋友,组织姐妹团、读书班、诗歌小组,编写既适合教工人识字、读书又能宣传革命道理的教材,以此提高女工们阶级觉悟,鼓动大家起来和反动派作斗争。上海五洲药厂青年女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徐鸿在回忆中谈到关露多次到其家中共眠一床、彻夜长谈,“关露同志为了深入了解我们工人受苦受难的情形和启发我的阶级觉悟,总是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顺着她提的问题进行思考,给她提供我们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情况”。
关露加入左联时,上海正处于日寇的窥伺之下,日寇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妄图侵吞上海。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关露成长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先锋战士和爱国诗人。在一二八抗战期间,上海闸北前线的炮火打得彻夜不歇。关露在左联负责人丁玲的领导下,冒着枪林弹雨,上街贴抗日标语,为伤兵救护募捐,还到闸北前线慰劳抗日将士。面对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积极抗战的鲜明主张。为此,关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始终站在艺术斗争的第一线,并发出倡议,希望“所有的文艺作者们,都应该站在救亡的统一战线上,创作挽救民族,反抗民族敌人的国防文学。所有我们的文艺作者们,也都应该使我们文艺的作品,作为反帝抗敌的武器”。
在此时期,关露将自己的理论主张倾注于诗歌的创作实践,写出了《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风波亭》、《太平洋上的歌声》等一批优秀作品。在《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1936年10月)中,关露以赤子之心,追忆故乡之美,诗人以一系列的“梦见”,用梦幻般的细腻笔触,舒展出故乡的原风景:壮丽的祠堂、雨后的艳色的阳光、青翠的稻田、在秋天的明月里青蛙歌唱、清净的池塘、二月的冰山、西山的古槐、早春天的北戴河等等。这些沉淀在诗人心中的故乡风景与情愫,却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荡然无存。面对日寇淫威下的“故乡”,关露激昂地呐喊:
你待救的呼声
已经把四万万同胞振响。
故乡,
我曾在你怀中成长,
我爱你,好像爱我的
父母,兄弟,忠实的朋友;
我愿意以我的热血和体温
作你战斗的刀枪,
我不能在这破碎的河山里,
重听那
“后庭花”隔江歌唱!
故乡,忆起你,
掀起我祖国的惆怅!
故乡,
我不能让你沦亡!
这些爱国诗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铿锵诗句,也为关露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美誉。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在打破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后,上海最终沦陷。孤岛时期,关露依然十分活跃,坚持以诗歌开展抗日斗争。她积极参加党的文总支部领导下的“上海诗歌座谈会”,并担任该座谈会出版的《诗人丛刊》的编辑。此外,关露还协助编辑由郭沫若命名、撰写发刊词的《高射炮》诗刊。在这一时期,关露创作爱国诗歌的热情高涨。1937年9月19日出版的《抗战》三月刊第十号上发表了她的两首诗:一首是《勇敢的军队———八百人》,歌颂了在日寇重重炮火包围中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另一首是《重建起自由的城堡》,则呐喊出四万万同胞坚持抗战的心声:“宁在焚烧后的短瓦颓垣上重建自由的城堡,把尸骨和鲜血,在胜利后祖国的黄土中埋葬”。此后,因组织安排,关露成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红色间谍”,深入魔窟,与狼共舞,放下了自己的文学之梦,舍弃了个人的诗人声誉,乃至牺牲了此后的人生幸福,以难言的悲壮行动背负起民族救亡的一份责任使命。
汪伪特工总部“76号”负责人、大汉奸李士群的“座上客”:“我不辩护”
1939年冬,关露收到一份电报,电文内容是“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署名是叶剑英,小廖是廖承志。当时的关露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但她明白党的纪律故而没有再问什么,于是按照上级指示到香港接受任务。在乘船途中,关露心中不停地猜想,认为组织上可能派她到香港办报或办刊物从事文化工作,如果是这样她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然而,事情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到港后,廖承志和潘汉年向关露布置任务,要她回上海做汪伪特务机关76号头目李士群的策反工作。李士群早年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又于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组建76号特务组织,残酷迫害抗日军民。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主席,成为臭名昭著、令人不齿的大汉奸。
从李士群的历史及为人特点来看,其本质上是一个投机分子。在投靠日寇后,李士群也想着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而,在1939年秋,李士群向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表示合作的意愿。为了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同意李士群的请求,有条件地与其建立某种联系,争取其将功折罪、提供日伪情报。出于谨慎,李士群提出由胡绣枫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员。李士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在李士群早年入狱时收留了其老婆,并且给予了很好的照顾,所以李士群夫妇对其心怀感恩,也非常信任。但是,当时胡绣枫与其丈夫李剑华正在大后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一时难以抽调出来接受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关露因为妹妹的关系与李士群相识,故而组织上决定由关露代替胡绣枫做与李士群的联络工作。
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关露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但潘汉年深知潜伏工作的危险性和艰巨性,因而反复嘱咐关露:“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当时的关露,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经历的心灵煎熬以及个人名誉上所要承受的沉重代价。接受任务后,关露迅速离港返回上海。此后,她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潜伏在李士群身边,观察李的思想动态,以便采取下一步行动,为策反工作做基础性准备。
由于旧相识且关露妹妹曾经的照顾,李士群接到关露的约见电话显得异常热情,特别安排警卫队长吴世宝开着自己的黑牌车接关露到76号总部。见到李士群后,关露以失业为借口希望在李这里讨个差事。其实,李士群基本上猜出关露的身份与意图,但在谈话中也只是点到为止。至此以后,关露成为李士群家的“座上客”。潜伏在李士群身边,关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当时靠做中学教师和兼职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为生,生活清苦,但为了掩护需要,又不得不穿着入时,周旋于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交际场合,过着完全违背意愿的生活。对此,关露曾向自己的好友、左联同事许幸之诉说在李士群家中的生活状态:“可是他们家那种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生活习惯,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啊!而我呢,既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更不会打麻将,像个傻子似的老呆在那里,陪着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玩乐,真感到格格不入。”
然而,更让关露难以忍受的是不知情的左联同事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对于自己的公开角色,关露已经感受到名誉的极大损害。由于关露接到的是秘密任务,所以当她踏入76号魔窟,成为李士群的座上宾后,左联同事们以及先前要好的朋友们对她避而远之,存有本能的防范心理。为此,有一次关露见到左联同事、好友蒋锡金时,为消解蒋的顾虑,主动说她已经忘记了蒋的住址,以此让蒋安心。当时的关露,不仅被隔离参加左联的日常活动,而且成为别人眼中的“汉奸”。
正因处在被误解的难堪状态下,关露向许幸之哭诉道:“再这么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许幸之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关露的悲伤情绪:“说着,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即便如此,关露仍然坚守岗位,坚定内心中炙热而深沉的信仰,并通过不懈努力和反复试探,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展开了一次关键性谈话,再次探知和确认了李士群的合作意愿。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李士群立刻明白关露的真实意图,随之对于自己的现状发了一通牢骚,一再说明身不由己才当汉奸,并表示愿意与中共开展沟通合作,为抗战做一些事情。
关露的坚守和努力,为潘汉年接下来策反李士群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2月,潘汉年和李士群第一次会面,地点在李士群的上海愚园路的家中,李士群在潘汉年的说服之下同意配合。此后,潘汉年多次与李士群见面,李士群也向潘汉年透露敌伪对苏北根据地所谓“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等方面的情报。抗战胜利后,关露到苏北解放区后,时任中共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对关露说:“由于你成功地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工作,李士群后来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日本鬼子要来‘清乡’,李士群就事先通知我们,并将敌人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们;我们要通过封锁线时,李士群下令将伪军调开给我们让路;他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李士群利用他的职权发放特别通行证,并派人护送我党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等”,对关露的潜伏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日本情报组织主办的《女声》杂志编辑:“穿上敌人的外衣干革命”
在帮助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后,联络工作改由其他人负责,至此关露顺利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实际上,在接近李士群的几年里,关露一直非常痛苦。她原本是一个诚挚朴质、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左翼女诗人,却偏要装扮成与汉奸流氓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样子。虽然内心挣扎纠结,但关露最终因信仰而坚持。当党派了新的联络员继续联络李士群后,关露就更加迫切地想早点奔赴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然而,事与愿违。1942年春天,党交给了关露新的任务:担任《女声》杂志的编辑。《女声》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即情报部)合办的一份中文杂志,主要面向中国女性读者,这实际上也是日本实施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而当时《女生》杂志的社长是日本著名的女作家佐藤俊子。为打入敌人内部,以隐秘的方式开展斗争,于是党指派关露加入《女声》,目的是:“在《女生》社社长、左翼作家佐藤俊子的左翼友人中,寻找日共的地下党员,通过他们获取敌方情报。”相比策反李士群来说,这次任务显然更加凶险。接近汉奸,关露就要承受如此之多的委屈;而委身日伪杂志,她更要将自己直接变成一个背弃民族的汉奸文人!
纵然任务艰巨,但关露还是服从组织安排,成功打入了《女生》杂志。在与主编佐藤俊子会面时,关露提出,“我学文学的,不懂政治,不会写政论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只爱风花雪月、不问时事政治的文艺青年。此后几年,关露巧妙经营栏目,逐渐把敌人的杂志变成了隐秘战线的斗争基地。在负责《女声》的“读者信箱”栏目时,她常常通过与读者探讨百姓日常生活的热点问题,宣传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比如:反对包办婚姻、“三从四德”,主张寡妇再嫁、男女平等的思想等等。在关露主持下,栏目办得有声有色。她发现进步青年,并把他们引向革命道路。虽然与大多数作者素未谋面,但她总能在大量投稿中,独具慧眼地发现思想上有进步倾向的青年积极分子,选用刊登他们的稿件,实际上使《女声》成为进步思想的传播阵地。她还以作品为武器,心中发出无声的呐喊。从1942年到1945年《女声》共出刊38期,关露用芳君、芳、兰、林荫、梦茵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包括130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剧评等。这些作品大多不涉及时事,主要是关注女性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展现出反封建的进步思想。
在《女生》杂志潜伏期间,关露的内心崇敬“精忠报国”的岳飞,却要无奈地扮演“卖国求荣”的秦桧,“穿上敌人的外衣干革命”。这种人格的双重叠加,实际上导致了她难以承受的分裂之痛。她在散文《秋夜》(1942年11月15日发表于《女声》第1卷第7期)中写道:“我愈觉得恐怖而畏怯,畏怯快要使我悲哀,我的眼睛快要流出眼泪,用眼泪表示我最后的软弱了。”但是,凭借着心中坚定的信念,关露毅然战胜了孤独的恐怖和怯懦,满怀希望、勇敢地走下去:“我不应该像刚才那样畏怯与恐怖,我不该感到寂寞与孤独,我不应该害怕风雨与黑夜。”即使身处黑暗的风雨里,关露仍然向往着风雨和黑夜过后,能够“看见一盏远远的明灯与明日的太阳”。
关露一方面坚守心中炽热的信仰,另一方面冷静地做好杂志编辑工作,因而受到主编佐藤俊子的信任,这让她得以比较隐蔽地开展工作。但是,在1943年8月,关露又将接受一项严峻的任务考验,不得不从隐秘状态转为“汉奸文人”的公开状态。这一年的8月,佐藤俊子让关露参加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就意味着,关露要以一个“汉奸文人”的公开身份登上日本本土。对此,关露深知此行将要承担的名誉风险,如果参加,自己的“汉奸”之名再也难以洗刷。因而,她一开始并不愿意,就在她想要放弃之时,她的上级潘汉年派人带来了一封信,让她抓住去日本的机会,亲自交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从而帮助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重新与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为了党的事业,关露不再犹豫,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之时,毅然踏上了去往东京的航船。
刚到东京,关露就故意装出水土不服的表象:或是“身体非常疲劳”,或是“感到剧烈头疼”,以此避开日方各种别有用心的安排。1943年8月,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粉墨登场,而日本方面为鼓吹大东亚共荣的荒谬论调,指派各色人物歌功颂德,以此粉饰其侵略的险恶用意。大会第二天,关露被日方要求以《谈谈大东亚共荣圈》为题作演讲发言。对此,关露非常反感,积极抗争,她向领队提出:“请你告诉日本人,我是学文学的,现在是妇女刊物代表,不懂政治,这个题目我不会讲。如果一定要我讲话,我自己想个题目,谈谈有关妇女问题”。关露的拒绝理由合情合理,日方不得不接受。在这次大会上,关露的发言题目是《中日女性的文化交流》,在其中关露谈到:“来到日本,有机会跟日本女性交谈,但因为互相语言不通,只好说英语,甚感遗憾。今后,希望中日两国的女性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能用各自的母语交谈。”在整个演讲中,关露没有丝毫宣传和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在日本期间,关露隐蔽而认真地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潘汉年交待的任务,而且收集了有价值的各种材料,详细记录了日本社会当时的思想动态。尽管心里充满苦闷,但关露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然而,东京之行对关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当她踏上日本国土,中国国内的报纸媒体便登出了大幅照片加以激烈声讨。而当关露回国后,立刻成为舆论鞭挞的对象。1944年12月21日出版的《时事新报》以大幅标题登载了一篇文章:《所谓大东亚女文学家———揭露关露之“秘”!》,详细剖析了关露如何从一个炫耀一时的进步女作家蜕变成为敌人宣扬文化的“汉奸文人”,对其东京之行更是予以责难:“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时期,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关露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她之附逆,既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没落,自愿出卖灵魂。”
身处舆论非难的风口浪尖,关露有口难辩,只能默然承受不白之冤。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全面胜利。接替佐藤俊子成为《女声》主编的关露感到无比兴奋,为自己的付出由衷欣慰,同时她终于不用再潜伏了!但转瞬间,在兴奋和欣慰之中,蕴含着现实性危险:国民党下达“肃奸令”,作为“汉奸文人”的关露也在抓捕名单之中。掌握这一情报后,党派夏衍等人赶紧把关露转移至江北解放区,关露也就此结束了深入敌营的潜伏生涯。
两度入狱、坐牢十年的“反革命嫌疑犯”:“我乐于做那填塞肮脏沟壑的沉默的水!”
为之奋斗的抗战取得全面胜利,而此时的关露作为“汉奸文人”却已臭名远扬,并就此影响了此后人生。到达淮南解放区后,由于不能对外解释自己曾经肩负的潜伏任务,关露没有看到鲜花、听到掌声,相反,迎接她的是接踵而至的打击。先是被隔离审查,而后她的恋人、时任中共南京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南京发言人的王炳南不得不接受组织上的要求,中止与关露的恋爱关系。更让关露难过的是,当她想重新拿起笔,打算继续写诗时,却被告知不能用关露的名字发表。
在失去爱情、丧失名誉的打击之下,关露的精神状况陷入崩溃,并因此而病倒。但面对这些打击,关露没有垮掉,更没有动摇心中对党的信仰。在向组织反映自己的情况后,作为地下工作者的真实身份得到认可,关露的党组织关系也得到恢复。对此,关露的病立即就好了,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生活中。在《卖花女》中,她化身一个长期在凄风冷雨的黑夜中孤独行走的“少女”最终寻找到光明和温暖,以诗人特有的炙热情怀讴歌对生命的礼赞和对自由的向往:
我生活在街头,
我是一个少女,
我的生命是春天,
我和花一样的美丽!
现在,在自由的世界中,
我看见太阳,
我踏上温暖的道路。
……
我爱我的容颜,
我的容颜和花一样盛开,
我爱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和春天一样光彩。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误解和潘汉年案的牵连,关露两度入狱、坐牢十年,但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仍然心怀赤诚,对党充满信心。1955年至1957年,关露被关在功德林监狱。在此期间,关露由于精神再次失常而喝痰盂中的水,因长期躺卧冰冷的水泥地而患上关节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关露再次入狱,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被释放。在八年的漫长牢狱生活中,为打发空寂时间,也为给自己打气鼓劲,关露每天磨一千次大钉子,最后竟将两枚大钉子磨成了两根针,这是何等的毅力和坚持!
出狱后,关露对于无妄的牢狱之灾看得很是淡然和豁达,她甚至还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调侃:秦城监狱的伙食不错,有抽水马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十年的牢狱生活,关露没有丝毫怨言,在给其侄女的信中坦然地写道:“有个偶然的机会被党彻底审查一番也是好的。也是一次考验,一次锻炼,一次教育!我感到我现在比过去坚强,某些地方提高了,我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在狱中拟好题目、后来创作完成的《告诉党》中,关露饱含深情地向党诉说自己内心的清白和坚定:
如果说,
共产党是我伟大的母亲,
真理就是我的祖母,
圣洁名门的子孙,
谁能够将我污损?
被真理的庄严所指导的
我的言行,
不能不端正;
被党的光辉所闪耀着的
我的生命,
没有半点灰尘!
1975年关露被释放,但与1957年一样,对其审查结论依然没有完全清楚,她的政治问题还有待彻底解决。关露出狱后得了脑血栓,她在病中开始整理关于潘汉年的历史证言和自己的回忆录。她曾经对丁玲说,“我不能死,我要为潘汉年等到昭雪的那一天。”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关露作出公正的平反决定,推倒之前对关露的诬蔑不实之词。可是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她,此时再也无力拿起心爱的笔尽情创作了。同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关露最后的牵挂已然了却。1982年12月5日,关露支走身边保姆,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后,与世长辞。
天理昭昭不可诬。1983年8月22日,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后,中央公安部正式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1955年6月后,关露同志受到了错误的逮捕审查,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关露,是一个曾被历史尘封的名字。恰如在自己诗作《没有星光的夜》中所隐喻的那样:“有人看见你死/但是不知道你是为谁而死/也不知像这样死去了的是谁。”关露,更是一个值得历史铭记的名字。为了民族的大义,为了在党旗下的誓言,关露用比自己生命还值得珍惜的个人名誉践行和坚守着共产党的理想信仰。她曾经这样解读过自己,“我乐于做那填塞肮脏沟壑的沉默的水”!在那些深入狼穴、斗智斗勇的峥嵘岁月里,在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紧要关头,关露为了心中炽热不熄的信念之光,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经历,她的光辉事迹令人动容感叹。
今年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这是一个伟大的纪念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为了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像关露一样献身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无数中华儿女付出了巨大牺牲,今天的我们更当永远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继续沿着他们的历史足迹,在党的领导下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