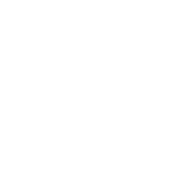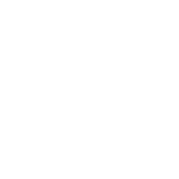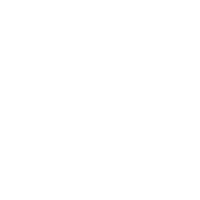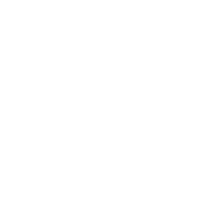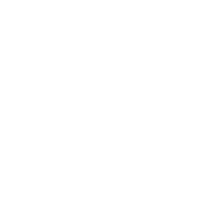吴 镕 口述 诸纪录 整理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农村改革都40周年了。回顾往事,听到的、看到的、自己经历的,都历历在目。改革波澜壮阔,留下许多可记可说、可歌可泣的历史。其中,有三件,我感到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里,我说一说,以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一个理论突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的包产到户,上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温州地区就搞过。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在河南新乡、洛阳,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和安徽、贵州一些地方又自发蔓延。据统计,1961年达到全国生产队的五分之一左右。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支持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所反映的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更是多次向毛泽东主席陈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恳切愿望,但都被严词拒绝。在1962年9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包产到户问题被作为“农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提了出来。那些搞包产到户的地区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行为”而遭到严厉打击。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粉碎“四人帮”后,贵州、内蒙、安徽等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农村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局限,仍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重申了过去长期以来“不准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
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长期禁锢农村干部群众的思想桎梏。三中全会结束后,安徽省委派工作组到肥西县山南区宣传全会精神,人们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省委书记万里主张“在山南地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加上此前1977年下发的省委“六条”,安徽省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有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万里说,对下面这些做法,我都没有表示反对,更没有加以制止,实际上是默许和支持了。四川省委1979年1月决定全省实行休养生息方针,包产到组的不少,一些地方又将地分包到人。
正当大包干“又生”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的语气很重: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地方,必须认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张浩来信引起了轩然大波,议论大哗。张浩家乡洛阳地区革委会一领导作打油诗一首:《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弄得群众没主张。
最热闹的是正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的七省三县农委负责人座谈会。与会同志争论热烈。激辩的结果有两大贡献:一是会议纪要上写上“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二是“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判、不斗争、不强制纠正”。这两条上报后,华国锋表态同意。华国锋当时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允许深山偏僻区孤门独户包产到户和对已搞包产到户的不批不斗,对以后农村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算是开了一个口子。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吸收了上述两点“共识”,指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变“不要”,一字之改,由命令改成了商量。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上争论热烈。在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发言讲到准备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立即表态说:“我们不能搞那个东西。”池必卿回答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位书记的话都上了会议简报。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这个文件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和基础。文件为包产到户上了个临时户口:承认它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那它本身到底是什么,当时还没有从本质上予以回答。
事情的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讲明确了,各种责任制都姓“社”不姓“资”,请大家去掉顾虑。
理论的飞跃和突破是1983年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至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终于在中央文件里面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合法形式确定下来。
1982年底之前,江苏对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争论激烈,波涛汹涌。安徽省在农村改革之初开展了大包干试点探索,徐淮地区开动宣传机器,“不准包产到户的妖风刮到江苏来,要守住江苏的北大门、西大门”。省委多次派出调查组暗访安徽,明查本省泗洪、沭阳等县,面对同一实际,结论却迥异。有的说“平安无事”,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有的说“暂时看来不错,但易滑向单干,滑向资本主义”。我也参加了调研,题目是纯客观的《谈话记录》,附上各种责任制形式的产量对比。如实汇报说,从层次看,上层坚持反对的多,基层特别是农民和村干部赞成的多;包产到组比不包的增产多,包产或包干到户增产更多。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春到上塘》长篇通讯,介绍泗洪县上塘镇垫湖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省委主要领导下决心亲自下去看,最终促成了江苏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开会讨论中央一号文件,万里还问我:“你们那一位(指省委主要领导)思想通了吗?”我答:“通了。”
提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一个破天荒的理论突破。1983年一号文件这段具有重大理论突破的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薄一波称赞中国包产到户,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同志一再肯定。
林子力之所以有这样的贡献,在于他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一贯有理论创新。1977年6月,他就与有林等同志著文《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当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全文播发,被当时人们称为十年浩劫后思想拨乱反正的“第一只报春燕”。
一场意义深远的思辨
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一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争论不断,坎坷曲折。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叶剑英同志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出:“使我国农村逐步变成农工商经营的富庶的农村。”
正当农民兴高采烈准备大力发展社队工业的时候,碰到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一些人利用此,把矛头对准社队企业,有的说“社队企业是乘乱发展起来的”,有的说“社队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劣挤优,与城市大工业争能源、争原料、争资金”,主张“限制”“收缩”“关停一批”,“小毛驴也要下”。而有的领导说,经济调整,关停并转企业,不包括社队企业,“这些小厂虽然落后,但当地需要”“小企业关停多了,市场东西就少了,把刚搞活的市场又搞死了”。
1981年2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就“挤”和“争”的问题,带队到江苏调研。结论是:总的说来,社队机械工业的产品,对国营大厂有挤有补,目前补的多一些,挤的少一些。薄老说,我是山西人,关公老乡,带着大刀,看来这大刀还砍不下去。
1981年2月,中央决定“加强对经济领域中不正之风的斗争”。按中央文件精神,社队企业不在这个范围内。但一些人把矛头引向社队企业,有的说:“社队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还有的对社队企业发祥地的江苏和无锡进行指责,说“发展社队企业富了地方,穷了国家,社队企业满天飞的活动,以物易物,冲击了国家的计划,大方向上有问题”。后来中纪委调查并听汇报,总的意思是社队企业不正之风确实存在,但都是生存逼迫的,是受害者,而不是害人者。中纪委负责同志说,社队企业是老百姓办的企业,要把老百姓和国家工作人员区别开来。
从1981年11月开始,国家组织了全国性社队企业大调查,到1982年2月基本结束,农业部起草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然后多方征求意见、修改完善。1984年3月1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即中央四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并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争议了两年多,告一段落,从此开辟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首次乡镇企业展览会。王震剪彩。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田纪云副总理参观时,希望田副总理写篇文章表示支持。田副总经理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国家经委主任)写吧。”顾省长说:“我们写好代拟稿,因为有些数据写上,省得吕主任查了。”吕东当即笑允。9月24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了吕东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江苏有突出贡献。1978年9月,根据国务院要求,全国农垦系统开展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学习南斯拉夫“贝科倍”经验。后来我省农垦黄海农场流传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说法。苏南地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也说,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商富起来。两句话上报中央,万里很欣赏,多次引述。1984年2月万里同志在烟台调研时向当地干部作了一个报告,报告说:“要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我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了江苏省的经验,谈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对乡镇企业,要推动它更快地发展。”
但即使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了,也不等于一帆风顺了。1985年粮食减产,社会上包括上层都有些议论,认为“无工不富”的声音太响,盖过了“无农不稳”。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跑步前(钱)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又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答辩文章《不正之风的风源》,认为北风、乡风、南风(改革开放)三个源头要仔细分析。
在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议论纷纷的当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农村问题论坛》1986年第86期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论文,他既肯定了江苏这个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指出,三句话,特别是前两句话,也的确有其不足之处。“如果我们认识只限于无农不稳,就会合乎逻辑地产生这样一种思想:我这里的农业已经发展到足以使社会政治生活‘稳’的程度,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大力发展农业了”。他同时指出,无工不仅不富,也会“不稳”。如果不指出和重视这些“不足之处”,会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为了表达对于老论文的思辨,我在同一刊物第98期上,写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并在《经济日报》上刊出一篇《三句话是“三位一体”》的文章,表明群众创造的经验,形象、生动地阐明客观规律和事实,无可指责,不必求全。我在文章中说,无农不稳,并未排除农业也可成为致富之道,但当时从总体上看,单一农业经济难以致富。无工不富,并非排除“无工也不稳”,要因地制宜。无商不活,也没有“排除商业同样是富和稳的条件或前提”,而且当时的情况,“流通问题往往大于生产问题”。江苏农民创造性提出的三句话,至今没有过时,现在提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句话的思辨,一直反映到上层。中央主要领导听说后,关照我们不要再争论。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工业兴起后,就富起来了。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把二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抵触的。
这段话,为这场思辨作了很好的结论。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口号。”
一个共识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
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
经济学家林子力等同志跑了几个省,调查了60多个涉及雇工的单位,指出了雇工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他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同志作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2到3个学徒、3到4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 就流传了“七下八上”,即雇七人是小业主,超过八人就是资本家了。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祖宗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人也不大够。
开会争来争去,加上下省区调查研究,大多数人当时取得了六点共识:
一、中国这么大,地区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共性的东西。
二、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同志说的,再看几年。
三、马克思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四、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生产关系。
五、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验、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六、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不能捣巢伤卵。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中央1987年五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个体经营者为了补充自己劳力的不足,按照规定,可以雇请一二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三五个学徒。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采取逐步引导的方针。
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的已大有人在。这就大大突破了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结语
三个重大问题的突破,立首功者是杜润生同志。许多人士都尊他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自谦地说,这是个团队,我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他带队研究起草了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和一个五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开放打开新局面。杜老指导农村改革,善于倾听老中青和各方意见,善于协调折冲和上下互动,化解难题,求得最大公约数和最广泛共识。几十年过去了,起草一号文件时杜老的民主作风、务实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亲自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尊重基层创造,善于将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经验进行加工、提炼、总结,用之指导全国。一号文件凝聚了老人的心血和智慧。
改革开放20周年时,我参与编写了《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当时85岁的杜老不要别人代笔,亲自写了《序言》。文章深刻阐述了农业家庭经营的理论基础:家庭经营适合农业生产特性、规模可大可小、农民拥有自主权、可以激活土地流动性、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他多次说到,农村改革的本质是还权于农。
2015年10月2日,杜老以102岁高龄谢世。我于当天致唁:“杜老率团队,三农保乾坤,业迹经天地,遗泽润生民”。我回忆农村改革开放之初的三大理论问题,也再次表达我对杜老这个百岁老人的深切缅怀。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