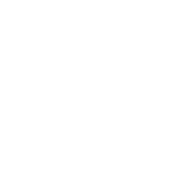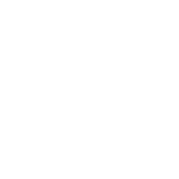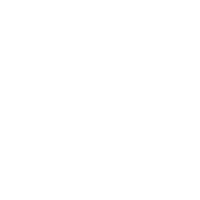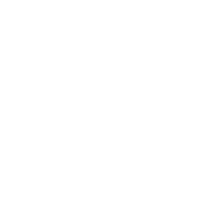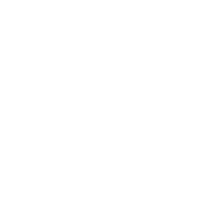李一氓是一位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和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兼具多重身份:诗人、书法家、版本目录学专家、收藏家……陈毅同志曾赞誉他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谈到一件作品,学术泰斗钱钟书说,能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则深情撰文纪念“这位可尊敬的、为红学立了功的老人”。
坎坷跌宕 抱朴求真
1903年2月6日,李一氓出生于四川的彭县,本名李国治,后改名为李民治,1928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用笔名李一氓,并沿用终生。1912年,李一氓就读于彭县北街秦省公立小学,与“五卅”惨案革命烈士何秉彝是同学。1919年春,在成都储才中学、联合中学读书,与革命烈士李硕勋是同班同学,拜把兄弟,友谊一直延续到1931年李硕勋在海南岛牺牲。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李一氓积极追求真理,1921年出川赴沪,先后就读大同、沪江、东吴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李一氓自上海赴广州,投入实际的革命工作。北伐时,李一氓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1927年,李一氓在南昌起义中任参谋团秘书长。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至瑞金时,他与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部队在广东揭阳流沙被打散,李一氓经汕头、香港回上海。
血战和溃败没有动摇李一氓的意志。回到上海后,李一氓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更为艰险的地下工作,主要是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翻译马列著作,并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负责协调上海文艺活动,因工作与鲁迅先生有所交往。
1932年,李一氓奉命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长征途中,李一氓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先后任特种营教导员、总政宣传部宣传科长,还同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等一起,担任干部团“上干队”(上级干部队伍)政治教员职务。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李一氓被抽调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近两个月。后又因工作需要,先后担任中共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
西安事变后,中央电调李一氓接受新的任务———作为毛泽东的私人代表回四川找刘湘开展统战工作,不期刘湘已离川赴汉口。不久,李一氓又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秘书长。
1941年,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李一氓脱出重围后,历经艰险,由徽州而金华,再奔桂林,转香港,过上海,终于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并将自己亲身经历“皖南事变”的实际情况分别在韶关和香港撰写系列电文报告党中央。由于按照项、袁的意见脱离部队不到10小时,李一氓自认为“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并“二话不说,决然接受”了经华中局提出的、中央批准的、 由刘少奇当面宣布的因“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而给予的口头警告处分。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作为叶、项之间缓冲人之失败。但作为当事人,他也实事求是地忆述了相关的人事,并慎重、磊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做出的时间距战斗结束日仅隔一天,情况不可能十分清楚,“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
皖南事变后,李一氓历任淮海区、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又先后担任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等职。以后李一氓辗转山东各地,曾任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和大连大学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曾任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文革”期间,年近七旬的李一氓遭受残酷迫害。出狱后李一氓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顾问等职,对被搞乱了的对外联络工作进行整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一氓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先后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1982年,李一氓不顾80岁高龄,满腔热忱地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1990年12月4日,李一氓在北京因病逝世。
大革命前就入党,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瑞金时期已身负国家保卫局部长的要职,抗战胜利后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主政一方……这些他人眼中传奇般的经历和荣耀,在李一氓的回忆录中写来却是那样的朴实无华,甚至自谦是“很平庸的”。他长期跟随周恩来从北伐转战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私人代表,又曾与刘少奇、陈毅在苏北工作共事,与鲁迅、郭沫若等名人交往也很多,但李一氓从不挟领导、借名人喧哗自重。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待领导、名人,有事时坦然提到,无事不攀,更无过多铺陈渲染。
历经坎坷跌宕,李一氓始终未改其纯朴本色和宽阔胸怀,这也最后集中体现在他感人肺腑的遗言中:“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
情系文化 孜孜不息
尽管在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但李一氓对文化事业似乎情有独钟,与之结下的情缘也最为深厚。
李一氓出生于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但自小就对国文、书法、绘画颇多兴趣。能写钟鼎文、种千株菊花的国文教员,在县城以画出名的二哥,成都元宵夜大摆春灯诗谜的雅况……都在李一氓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迹。五四运动后,李一氓广泛阅览包括《新青年》、《向导》在内的各种杂志。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李一氓先后出版了《新俄诗选》、《马克思恩格斯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等译作,参与了进步刊物《流沙》、《日出旬刊》、《巴尔底山》的编辑和写作工作。
以后戎马倥偬和公务繁忙,李一氓往往随缘随遇而学,但态度竭力顶真,每有妙得深悟,又敢于秉笔直书,一抒己见。故其一生著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学戏曲、古籍版本、美术碑帖等诸多方面,且大都颇具学术与珍贵的史料价值。如长征结束不久,李一氓凭一个简单的日记和还很清楚的记忆,写了一篇纪实文章《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被收入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重走长征路,在读了李一氓的文章后,专门给李老写信,感慨他的沿途印象与李老的记述完全一致。再如1939年,李一氓在《抗敌报》上发表了《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一文,见解深刻,行文利落,对澄清当时的思想认识起了重大作用。直至晚年,李一氓还不断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潜心研究,并带领同志们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在李一氓的著述中,最为意趣盎然的大概是记述其一生烹饪经历的《征途食事》。李一氓是四川人,不仅会吃还会做。《征途食事》中关于长征路上的一章以独家的第一手材料,向世人记述了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长征食事。例如,他写道:“除大锅饭外,行军驻下来总有自己做东西吃的机会。行军路上,很难找到茶叶,茶叶无法假造,就假造咖啡。饭后,弄点麦子来用油炒成接近炭质时,下半瓢水,一煮,水色变黄,带苦味,无糖,加点糖精,一杯咖啡就出来了。这成为我们几个人长征中经常用的办法。”再如:“长征生活最苦的一段当是在川西北的两三个月。那时把口粮包干了,不开大锅饭,每人分的口粮规定吃五天,实际上我两天半、三天就吃完了。准备大饿两天。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行军到一个地方,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萝卜干,还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这可救命了。吃了黄油,不禁精神抖擞,我相信它的营养价值极大。那时,董必武同志同我们一路行军,有个同志送他半只野羊腿,他知我们有点烹调本事,就交给我们做,讲明平均各分一份,我们当然乐意接受这个小任务。”多遍拜读之后,笔者深感《征途食事》中长征一章写得实事求是,艰难困苦、豁达乐观都描写得合情合理,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除了长期亲自笔耕不辍,李一氓还十分乐于、善于组织文化活动。如1943年11月,李一氓在苏北淮海地区主持工作时,积极牵头成立了湖海艺文社淮海分社,与陈毅等在盐阜发起创设的湖海艺文社文字唱酬、声气相应。差不多同时,爱好京剧的李一氓看到淮海区的干部中会唱京剧的不少,又动了组织一个京剧团的念头。先是花一笔钱,去大城市买来“行头”,然后选调集合人员,制备好舞台装置,又挖好横沟做观众座位,最后演出时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效果不错。不料没几天就有人向华中局告状,“罪名”是不艰苦奋斗,买行头,唱旧戏。幸好1944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文章也已由延安广播,李一氓就凭这篇文章的内容,“闷声不响”地改编出京戏脚本《九宫山》。《九宫山》人物众多,气势恢宏,讲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历经挫折取得胜利又最终失败的悲剧。接着赶紧彩排、连场公演。当时在根据地戏剧演出极为少见,加之又可以作为整风学习的一种辅助形式,结果《九宫山》受到了干部、战士、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轰动一时。告状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受其影响,以后整个淮海区各县相继成立了文工团,每个村也都有了演出队,文化生活一时异常活跃。
1982年,鉴于李一氓在古籍文献方面的素养和功力,中央委以领导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的重任。此时李一氓已年届耄耋,却豪气不减当年,亲自对整理古籍的下限、重点和先后缓急以及新领域的开拓,古籍整理的手段与方法,古籍整理的最终目的等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辛勤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在李一氓的主持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3500多种古籍得以重印流传,其中皇皇巨著《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李一氓的学识和人品也令专家学者们由衷钦佩。如钱钟书后来年岁大了一般会议是不参加的,但氓公召集古籍整理小组会,就可以把他请到家中。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再如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曾撰文《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记述了“红学史上的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以此来“纪念这位可尊敬的、为红学立了功的老人”。事情发生在1984年,初闻李老决意向苏联洽商出版列宁格勒所藏《石头记》旧抄本,周汝昌颇感意外又很高兴。很快李一氓亲自“点将”周汝昌等专家访苏验书。但到了规定日期,1984年的12月,周汝昌考虑自己年已66,隆冬时节赴苏联严寒之地,颇有顾虑,兴致不高,遂专函向一氓请辞。但“李老意厚,不获许”,只得“勉力奋勇而行”。待到列宁格勒的博物馆藏书阅览室坐定,放大镜下亲验抄本,竟有奇迹入目! 周汝昌写道:“原来,曹雪芹虽然大才,却因传写黛玉林姑娘的眉、目而大感为难,甚至有‘智短才穷’之困,以至《甲戌本》上此句(首句叙写黛玉容貌时)这两句竟未定稿,留着显眼的大空格子———而其他抄本之不缺字空格的,却是后笔妄补之文,非芹原句也……今日一看苏藏本,竟然整整齐齐地写作‘……罥烟眉’ ‘ ……含露目’! ……草草再往后翻看几处……但心中已无疑问:此本价值,过去低估了,这才真是一件多年来罕遇的奇珍至宝。李一氓先生他老交付的这一重要任务,总算勉强胜任了,没有辱命。”弄清了林黛玉眉眼的周汝昌惊喜交加,对李一氓更是感佩不已。而李一氓事后也为访得苏藏本《石头记》喜而赋诗(诗前附序):
《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约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极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莫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即谋付之影印,以飨世之治红学者。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返京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诗书俱佳 抒吐衷肠
李一氓写旧诗始于中学时代,自嘲是因为“偷懒”,一首诗,五绝七绝不过二十几个字,五言律七言律不过四五十个字,相较长篇大论容易交差。大学期间李一氓读了不少宋词,兴味颇浓。1927年到1933年李一氓写过一些新诗,其中有一首《春之奠》是为了悼念苏联顾问铁罗尼的俄文翻译纪德甫(随北伐军攻打武昌时不幸为流弹所中,牺牲在李一氓身边)而作,发表在1928年3月出版的《流沙》第一期上: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生机之能灭了,
一般这便是“死”。
但他们说你永生,
你负有“烈士”之名。
我亲眼看见是,
你的血并未染出半朵自由的鲜花,
从棺材中把一点一滴的尽浸入泥沙。
至今有谁记着?
土冢中怕只有子弹与枯骨相亲地长眠,
唱出“不朽”二字,白杨树上的啼鹃。
糢糊的影像里,
高不过五尺,围径不过一丈的馒头一个,
不是丰碑,是细长的木牌上题着“阵亡将士之墓”。
前年的春天,
我们在炎炎的南国相见;
今年的春天,
我高举起一杯苦酒相奠。
武昌城外怕已生磷的枯骨之魂哟!
以后李一氓几乎没写过新诗,但零零星星写了些旧诗文。其中很多是为英勇牺牲的战友撰写的挽联和悼诗。1942年,他在《新知识》杂志发表了诗作《七•七感怀》:
触目四郊多敌垒,半年游击出张圩。
琴书冷落诗人老,慷慨平生付马蹄。
七月战云仍黯黯,六塘堤柳自青青。
新辛风景元须泣,泗上蜂屯子弟兵。
北渡三年多战迹,南征残腊有冤魂。
徐扬淮海无余子,青史难湮新四军。
这首诗风格沉郁深婉,残酷艰巨的战争给淮北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撼人魂魄,而慷慨激荡的抗敌豪情又催人肝胆。
1946年3月,在刘老庄82烈士牺牲三周年之际,李一氓亲笔为烈士碑撰写碑记,又在墓门前题写了一副雄浑悲壮的挽联:
由陕西,到淮北,敌后英名传八路;
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
李一氓开始大量写词,则应追溯到皖南事变之后。军部几乎全军覆没,个人又备尝艰危,1941年的元宵节夜,盘桓桂林已多日的李一氓感慨良多,写就一首《绛都春》,也不加上下款,直接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如李一氓所料,郭沫若一看就猜到是谁写的,并汇款几百元。不巧李一氓已离开,没有亲收。1942年底,李一氓又遥寄郭沫若一首《念奴娇》,中有“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句。
自从写了《绛都春》,一直到1949年,李一氓依腔托韵,“颇为沾沾自喜”地写了上百阙词,再加上诗,汇集成一个抄本。因皖南事变中有渡江一案,又取东晋祖逖中流击楫的豪迈之意,故题名《击楫集》。1949年以后,李一氓很少写词,七言绝句则写的较多 。渐渐的,《击楫集》中诗、词各占一半。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风暴来袭,李一氓忍痛将唯一的《击楫集》誊清本付之一炬,演了一出“焚稿”。即使如此,造反派还是从《流沙》和李一氓先前出的一本油印本《赣游诗草》上面去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指责他在庐山上的一首诗:“筐篮篓袋杂纷陈 ,小市梧桐树下成,买得梨瓜三五个,日中交易利民生。”是反对大跃进,主张自由市场,提倡资本主义。
1966年到1973年,没有作词赋诗的环境。1973年10月,因皖南事变接受“拘留审查”长达5年的李一氓被宣告无罪释放。劫波初渡,感触纷如,李一氓又开始诗词创作。以后陆陆续续,写就不少感事怀人之作。如1978年曾仿李商隐体作《无题》纪念好友潘汉年(1955年因“内奸”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1982年平反):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李一氓与潘汉年1926年底相识于南昌,短暂的几个月相处,已“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1927年至1932年,两人在上海并肩作战,配合默契。以后数度相逢、分开。对于此诗,李一氓曾如此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文革后,一些热心的同志把还留存在手中的油印本《赣游诗草》送给李一氓,再加上一些从各处搜集来的旧作,以及新作,略加删选,又可汇成一本。因惋惜当年那付之一炬的誊清本,希冀其浴烈火能重生,故诗词集仍取原名《击楫集》。
除了诗词创作,李一氓于词书的鉴藏上也用功甚深,一生收藏的词集总计约2300余册。他还择宋、明、清诸佳本详参互校,亲手编成了《花间集校》。该书现已成为词学的经典版本。
与诗词相较,李一氓似乎并不太看重自己的书法。但经行家品鉴,其书法敦朴雅逸,笔法、气势别具一格,颇堪寻味。其晚年作品多行草,字与字之间很少游丝牵引,但笔墨变化丰富灵动,一字中常有一笔或数笔粗壮淋漓。概因少年学书的童子功不弱,又得多年故纸堆的浸润熏陶,故往往率意挥洒,就兼具颜鲁公庄重刚劲的骨气与文人学者儒雅秀逸之风韵。然细细品味,似又可辨出那特殊的历经“电闪雷鸣”之后的沉着透脱,令人不由揣想当年李一氓从秦城监狱转到阜成路304医院后,每天都要写上十来张拳头般大小毛笔字的往事。
云烟过眼 大爱无私
李一氓与收藏结下半生之缘始于1945年抗战胜利。当时,淮阴、淮安、高邮、泰州等颇具古文化传统的城市相继解放了。在淮阴城,部队转移时,李一氓看到有的战士将字画铺在地上睡觉,转移时留下也无人收拾,觉得十分可惜,就让警卫员一幅幅卷好收起来。李一氓又向熟识的指挥员同志们打招呼,遇到这种情况,就帮他收好。一时弄到了几十种字画,中堂、条幅、收卷、册页……皆有,山水、花卉、人物俱全。为了搞清字画的作者,李一氓又兴致勃勃地寻来《画史汇传》翻查,这样渐渐对收藏发生了兴趣。在当时淮阴、淮安日常的小市摊上,李一氓也淘到过一些宝贝,如两张散页的郑板桥书法、一方金农款的歙砚,再加上高邮的同志们给他送来的东西中还有明吴去尘制的墨、王伯申的书法、王小梅的花卉等。日积月累,李一氓的宝贝要几只大箱子才装得下,闲时细细展玩,好不惬意,但一出现军情,就成了大包袱。一些来自农村的战士和中下级干部,对于李一氓同志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认为,战事紧张,弹药、粮草都要驮运,抽出几匹骡子一天到晚驮着几大箱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奔波,太不值得。有的同志还直接找到陈毅同志提意见。幸好陈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说:我们共产党是打天下的,也是要坐天下的。李一氓同志箱子里的东西,看来平常,其实全是国宝,不能丢啊。大家眼光应该放长远些。
1949年进北京以后,李一氓常常跑琉璃厂。一开始主要收藏字画和一些有关词的书籍。因财力有限买不起宋元的字画,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末清初的东西。其中石涛的手卷、册页收得比较多,还有张学曾的一大幅绢本山水、龚贤的两幅山水。字画之外还收藏了一些陶瓷、明清墨、漆器、砚台等。
以后字画价格逐渐贵起来,收藏小说、戏曲、木刻画三类书籍又颇为“时髦”,李老就跟着熟识的朋友如郭沫若、郑振铎、齐燕铭等竞相购藏起来。大家一起在琉璃厂争书,又相约拿出新到手的东西来交流,一些书缺页缺版,也可相互借阅抄补好。李一氓收的书,以明本居多,从种类上讲,以词书最多最好。故李一氓一直引以为傲,曾与郑振铎约定要拿出词书来好好比一比。然而1957年郑老坠机异国,此雅约终无从谈起。
驻外和出访期间,李一氓也总爱逛当地的书店。这样坚持不辍,收藏日丰。到“文革”期间造反派抄家时,北京图书馆“很苛刻”地挑选接收了李老图书4607册,其中,中文线装书3454册;北京图书馆不收,转为首都图书馆接收的也有两千多册;另外故宫博物院接收的字画古董也有三百多件。
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通知北图、首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将书籍字画古董等退回,李一氓却决定要将自己的珍藏无偿捐献给国家。1977年以后,有同志劝他把一些珍宝从北图和故宫要回来,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始终不悔,以为“捐就捐了,义无反顾,何必再要,只要我凭良心对得起国家文化事业就行了”。时光流逝,年岁渐高,李一氓又将身边留存的明清善本、2000多册词书、古陶瓷等分别捐赠给家乡的四川图书馆、四川博物院。
当曾经熟稔和珍爱的书籍、古董被搬运一空,书房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有一段时间,本就不苟言笑的李一氓更为沉默了。他常坐在房中,闭目沉思,半天不说一句话。或许,在他的脑海,有一幕幕荧屏闪现:几多痴迷、几多艰辛、几多遗憾、几多感悟……抑或,他是在静静享受那无私奉赠后的廓然无累与寂然欢喜。以后,在记录其收藏生涯的文章《过眼云烟》中,李一氓写道,“我的这一点东西,对于我真是云烟过眼了。但它们依然是云,依然是烟,依然在北京和成都悠悠而光彩地漂浮着”。
(责任编辑:艾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