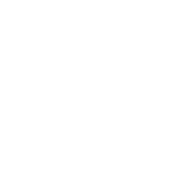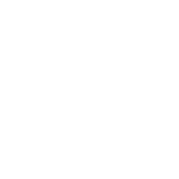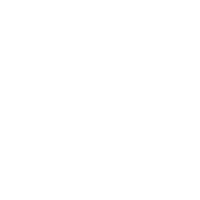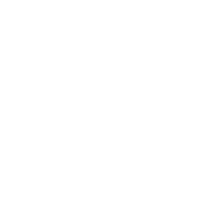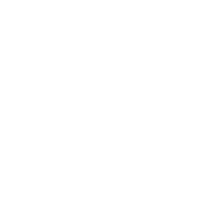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青年知识界对“信仰的主义”燃起精神渴求。五四时期传统价值体系崩解而新信仰尚未确立,引发新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困顿:前辈在传统与现代间犹疑,青年面对多元思潮陷入选择困境。著名历史学家张灏指出,五四兼具怀疑主义与重建信仰的双重特质,旧信仰废墟上虚无主义弥漫,其思想源头多元。
周恩来是个心忧天下,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不断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旅日日记》是他1918年留学日本期间撰写的日记,真实记录了近一年的每日学习、生活、社交和思想情绪变化,特别反映了青年周恩来大量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从中吸纳比较各种思潮,思想逐步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
一、家国不幸和个人前途让他内心一片迷茫
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曾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说: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我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的报纸上看到一些。那里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
周恩来旅日时期,苦闷、抑郁、彷徨的情绪曾一度笼罩着他的心灵。这不仅是因为游子在异国他乡孤独难忍,而且因为像那个时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恩来经历了从希望到幻灭,又见到一线光明的思想历程。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李叔同深沉地唱出了时代的感伤和遗憾。
鲁迅埋首古籍,苏曼殊“逃释归儒”成革命和尚、奇人,李叔同“逃儒归释”归于平淡,以缁衣终其身。这些事例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亘古未有的社会动荡中饱尝彷徨苦闷,以及外来文化涌入后中西文化碰撞激荡中力求突破,面对内忧外患,寻求破解社会政治危机的迷茫。
周恩来同样是这样的心境。在南开学校时,有张伯苓为学子们遮风挡雨,使其得以安心求学、专注事务,如今他必须独自面对真实的世界。家国不幸、个人前途渺茫,既想考察社会现状,又需全力应对考试,周恩来深感压力巨大,内心陷入巨大迷茫。
1918年1月2日,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悼念嗣母陈氏去世十周年,将自己的思念写进《念娘日记》:
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个儿子没有?
1918年1月8日,接堂弟来信,得知留居淮安的叔父周贻奎在贫病中去世,异常悲伤,立志发愤读书,埋头用功,以考取官费留学生。随后搬到一租金低廉的住处,改包饭为零买,每天废止朝食,以节省开支。
二、唤醒新青年,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
周恩来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喜欢从报刊等当时的“新媒体”中获取重要信息。所以读报是周恩来青年时代很重要的一种学习和生活方式。旅日期间周恩来每天必做的一项功课便是阅读报刊。他曾说自己当时“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他经常到东京中国青年会阅读报刊杂志,了解各种新思潮,与朋友频繁接触,广为交谈。
东京神田区有书铺几百家。据一个和他同住东京神田区三崎町的留日学生回忆:周恩来“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里翻书阅读”。
除每天用一个多小时阅读日本报纸外,周恩来还注意观察日本社会。1918年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人都应该注意。”
可以说此时的周恩来像海绵一样地吸收着新知识。1918年4月3日,周恩来致信留美南开同学冯文潜,提到对“新思潮尤所切望”。以前他在国内没有机会接触到的“新学”,现在则是有点眼花缭乱。
成立于1917年的新中学会,是一个南开中学和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的爱国团体。这个团体的章程明确指出:以增进友谊、砥砺品德、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为宗旨。不过这个团体更倾向于提倡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念。周恩来在日本期间投身其中。
1918年春天,《新青年》杂志的孔教批判和文学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于国内的《新青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是读过的,但当时他的心思不在这,光忙着研究“汉学”和“古文”了,当然那时课外活动也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因此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对《新青年》未留下深刻印象。但大概是因为南开学校毕业之际,皖督张勋在京兵变复辟,他深感封建残余未消,旧制隐患不绝。而且大概是毕业之际受了蔡元培、陈独秀演讲的影响,周恩来在东渡日本途中乃至到了东京以后,开始对《新青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旅日日记》(1918年2月15日)中记载:“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3卷4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3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
2月16、17日,周恩来连着两天在日记里描述自己读《新青年》的感受,感觉似乎比一般人信仰宗教还要高兴十倍。这次大领悟让他感觉“重生”和“更生”,从此开始摒弃旧观念,开启新思想,追求新学问,做新事情:“这几天连着把3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周恩来还在当天的日记里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从诗句可见,《新青年》对他的思想启发之大。
《新青年》自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出版)起开始采用白话文和新标点。与此同时,周恩来的日记也从1918年1月1日起采取白话文,这从侧面反映了《新青年》对他的影响。此举标志着周恩来对文学表达的革新。
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刊载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鲁迅”这个笔名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出现,这部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开头的日记体小说,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里程碑。
在本质上,鲁迅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而非小说家。那么,在鲁迅的视角中,小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实则是一种“跨界”的尝试。因为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小说及其作者并不被社会所重视。鲁迅对新旧文化有深刻理解,为了推动文化的革新,甘愿放下身段,毅然走上了创作小说的道路。鲁迅将对中国人骨子里奴性的长期思考融入作品,迈出了成为伟大作家的第一步,也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
鲁迅的作品毫无疑问也对周恩来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关注俄国十月革命,使他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帝国主义围困中恢复战后创伤,推行新经济政策实现经济提速。伴随国力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大增,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十月革命爆发后,欧洲革命也进入高潮,爱尔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也都爆发了革命。这些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以共鸣、希望的笔调介绍十月革命,公开地发表于报刊上。所以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俄国十月革命已成为日本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
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从《露西亚研究》杂志中看到关于对俄国党派的介绍,还记录了列宁的名字。他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
他在日记中还对于这场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制度本质及成功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主张实行彻底民主并推翻资产阶级制度,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该党作为激进社会主义派别,因符合工农诉求而影响迅速扩大。这可能是周恩来第一次较明确地表述“俄式”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看来周恩来已经能够准确理解十月革命的“俄式”社会改造模式,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要按此模式“刷新中国”。
周恩来在日本还读了美国记者约翰·里德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采访后写的著名报道《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日本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很多先进知识分子都阅读过河上肇的作品。周恩来因此对十月革命、苏维埃、红军、国内战争的了解远远超过国内青年。
这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
北洋政府与日本密签军事协定的消息传来,一场捍卫主权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周恩来密切关注这场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使他暂缓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探讨。
1918年5月16日,日本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段祺瑞政府代表靳云鹏在北京秘密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双方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所谓“防敌”,实指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当时国际帝国主义正武装干涉俄国革命,日本企图乘机侵略俄国并独霸中国东北地区。该协定核心内容包括:中日采取“共同防敌”行动;日本战时可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境外作战时中国须派兵支援;双方战时互相供给军械及军需品。凭借该协定,日本大举派兵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取代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致使中国面临沦为日本附属国的危机。留日学生彭湃等在东京发起游行抗议,继而集体罢学归国,于各地组建救国团体开展爱国宣传。北大等各校2000余名学生赴总统府请愿废约,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亦奋起抗争。全国工人与工商业者更是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
1918年8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向西伯利亚进军,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兵力最多时达7.3万人。日本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暴动从7月23日开始持续到9月17日矿工斗争结束。这次暴动波及日本全国,57天内33个县都发生了暴动。这期间的7月28日至9月6日,周恩来在国内度暑假,虽未亲历日本暴动,但日本的“米骚动”对他触动极大,使他重新审视日本及其维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军国主义奉行“扩张领土”“有强权无公理”,是侵略之源、他国之害,不合于“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
日本的“米骚动”事件使周恩来认识到,日本的发展道路并不完美。国富和民强并不是自然关联的。他透过日本社会结构的内层,洞察到其中的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看到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他事后所描绘的,仿佛听到了茫茫黑夜中痛苦挣扎的“岛民”正奋力疾呼: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军国主义用镇压劳苦大众的斑斑血迹,擦亮了青年周恩来的眼睛,使他不再把号称“富国强兵”实则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军国主义作为可以拿来的“主义”。
为了筹办南开大学,1918年11月,严范孙和张伯苓漂洋过海,赴美考察教育,12月14日,抵达日本横滨时,南开留学生们前来迎接,并陪同至东京新中学会。席间,张伯苓说他回去后创办南开大学,在美国已请了几位专家来学校任教。大家回国后可以去上,也可以去美国,他从中帮忙。一席话把大家的心唤动了。
四、李大钊等人的文章,指引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两巨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北大红楼。陈独秀的到来,为北大带来了《新青年》杂志。而李大钊的到来,使得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变了颜色。章士钊后来回忆道:“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而这一年,中华民国上演了张勋开历史的倒车,康有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尽管他们的复辟迅速失败,却暗示了封建主义旧思想的根深蒂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国内的李大钊深受鼓舞。虽然革命爆发三天后就见诸国内报端,但因中外反动势力阻挠及报道混乱,李大钊转向日本进步思想界系统搜集资料。经潜心研究,他对革命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革命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他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认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希望中国人民迎接新的革命潮流。
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时,周恩来极有可能读过这篇文章,他当时正在国内。因为在日本已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回国后读到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他显然比别人对相关内容有更多的领悟。
1918年10月20日,回到日本的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可见此时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
1918年深秋,一战结束,蔡元培在京举办系列演讲,立足民族振兴与道德建设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同期李大钊作《庶民的胜利》宣言。恰值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李大钊在演讲中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庶民的胜利》首度向国人宣告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场革命不仅敲响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更开创了人类文明革故鼎新的新纪元。李大钊铿锵有力的讲演词,如同春雷炸响神州大地,在沉睡的华夏激起层层思想波澜。
演讲稿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起,奠定了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地位。
同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还创办了《每周评论》。李大钊在其中发表了元旦社论《新纪元》,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认为这场革命将为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带来划时代的变化,并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带来希望。李大钊此时显然已经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第一个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对旅日的周恩来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的。
然而1919年初的李大钊是有些孤独的。在中国知识界,李大钊的激情预见并未引起广泛反响,仅有少数学生追随。他在红楼的走廊里踱步,思索一潭死水般的中国。力量在暗中涌动。五四运动后,作为发起者和主力军的北京大学,在历史潮头掀起了巨浪。
河上肇所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创刊于1919年1月。《社会问题研究》从第1期起,就开始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河上肇自述:“1919年1月以来,我之所以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原因大概是那时找到了真理的方向,尽管不懂,却决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吧。我开始啃《资本论》,大约也是那个时候。”
周恩来留日期间较国内多数知识分子更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彼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尚无完整中译本,国人接触该学说难度极大。
除了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据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周恩来在日本还读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等著作,以及《新社会》《解放》等杂志。同时也阅读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其中,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著名唯物史观公式,帮助周恩来建立起对《共产党宣言》的初步印象。
周恩来东渡日本,本指望通过实地考察日本、学习日本,借鉴到“济世穷”的学问。然而,他对日本越来越失望了,于是决定“返国图他兴”。同时,由于频繁阅读《新青年》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导他逐渐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1919年4月,归国途中,周恩来用一首诗表达了他追求真理似有所得的心情: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归国的时候,周恩来的箱子里还带着马克思主义书刊。周恩来庆幸自己在日本接触了新思想,在迷茫中找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作者系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李曼容